• 心盲正在成为一个丰富的科学研究领域,研究者通过与心盲者的合作,深入探索人类大脑的复杂工作机制。
我躺在一个比我的身体略宽一点的白色圆筒里,被一堆房车大小的复杂设备包围着。这是一台功能磁共振成像机(fMRI),一项现代神经科学的科技奇迹。两个小充气垫紧贴着我的太阳穴,以固定我的头部。
“我们要开始下一轮练习了,”堀川博士温和地说道。我们现在位于地下,就在东京大学本郷校区医学部的一个实验室里。“你觉得可以继续吗?”
机器再次启动,强大的电流在我周围的低温冷却导线内流动。无线电波在我脑中奔涌,使得我脑中的氢原子偏离原始自旋轴,进而测量轴恢复的速度。对于周围的传感器而言,我就像一杯透明的水,大脑中任何细微的血流变化在这三维空间中一览无余。
几秒钟之后,一个夹杂电子噪音的合成女声传入我的耳朵:“高顶礼帽。”我闭上眼,想象着一顶高顶礼帽。几秒钟后,一声嘟嘟声提醒我用手中的评价我脑海里的画面有多清楚,我照做了。声音再次响起:“灭火器”,然后我重复着这个过程。接下来是“蝴蝶”“骆驼”,再然后是“雪地摩托车”,一个接着一个,持续了大约10分钟,与此同时,系统监测着我脑中突触的活动。
对大多数人而言,这应该易如反掌,甚至悠然自得。但于我却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因为我闭上眼时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每一个提示后,我都在0到5的评分中将我的心智图像评为“0”,因为一旦闭上眼睛,我看到的不是日常物品、动物和车辆,而是眼睑下的黑暗。我无法自如地在脑海中形成哪怕是最模糊的画面。不止如此,我也无法在脑海中产生声音、气味或任何其他种类的感觉刺激。
我患有所谓的“心盲”,即无法自动地想象任何类型的感官刺激。我知道什么是高顶礼帽。我可以描述它的主要特征。我甚至可以在纸上画一个相当不错的高顶礼帽图案给你展示,但我就是无法在脑海中将它可视化。我到底怎么了?
过往生活里,我或多或少对自己的特殊方面已有所意识,这有时让我痛苦:糟糕的记性,良好的方向感,和匮乏的“视觉创造力”等等。我总觉得这些特点莫名其妙且毫无关联,因此并未多想。毕竟,谁身上没有点古怪的地方呢?
然后,在2021年的某一天(果不其然,我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时间和地点),当我第一次了解到“心盲”时,就如当头一棒:当人们说“在你的脑海中想象这个画面”时,并不是在使用隐喻性词汇,他们真的能在脑海中唤起形状和颜色!这一突然的领悟促使我将那些微不足道的特点拼凑成一个单一自洽的现象,这一现象与对心盲的科学描述吻合。在正式诊断前,我已经相当确定自己就是心盲。
这些特质并不为我所独有。人们宣称自己缺少“心灵之眼”的零星报道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世纪的科学文献中也提及了几例这样的案例。然而,这些案例在广泛的科学界被忽视,并被视为是相关领域的异端或误解,因而被边缘化。
直到2010年代,这个话题才开始引起关注。一名男子向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认知与行为神经学教授亚当·齐曼(Adam Zeman)寻求帮助,声称在心脏手术后失去了自己的“心灵之眼”。2010年,齐曼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这名男子在试图想象事物时,其大脑活动模式与其他受试不同。[1]
这是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但在齐曼的论文发表后,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有几个人联系他,声称他们自打有记忆起就一直是这样。齐曼和他的合作者们使用“视觉想象生动性问卷”(Vividness of Visual Imagery Questionnaire,VVIQ),这一测试内部可视化性质的常见方法,来评估了这些人的说法,发现这些个体似乎确实几乎无法在心灵中按照意愿进行可视化。研究人员在2015年发表了这些发现,并提议称这种情况为“心盲”(aphantasia),在希腊文中意为“缺乏图像”。[2]
有了新的标签,心盲的相关言论开始在神经科学界和社会层面流传。世界各地更多的研究团队开始研究心盲,学术杂志每年讨论心盲的论文也层出不穷。我们现在知道,大约每25人中就有1人有心盲——说罕见也罕见,说普遍,每个人也都可能认识几个心盲者。
对于有着可靠的“心灵之眼”的人,心盲可能是充满困惑的经历。想象不出画面和声音,可怎么正常地生活下去呢?
关于心盲的最大困惑之源,就是将“想象”和“形成心智图像”混为一谈。这当然不对。我可以想象任何事物,只是这些想象都缺乏感觉表征。想象的对象作为相互关联的概念存在于心灵之中,有如一份关于事实的清单列表。例如,当我重新阅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主人公与大马林鱼搏斗的场景时,我获得了大量信息:我们坐在他的小艇上,在墨西哥湾波浪起伏的海面上漂游,灼人烈日下,那个可怜的老人连续数小时拉着鱼线。我能理解这个场景,尝试预测接下来的情节,并共情角色的处境。

让我惊奇的是,这些“概念清单列表”并非随意漂浮在虚空中,而是存在于我脑海中一个可操纵的、连贯的三维结构中。在《老人与海》的场景中,我可以想象自己在小船上四处走动,坐在圣地亚哥旁边,我可以“感受到”那条鱼漂浮在船附近时所带来的庞然大物的感觉。我能在黑暗中找到去卧室的路,或许也是拜这种空间意识所赐:即使看不见,我也知道家具的位置和物品之间的大致距离。至于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能不靠图像形成空间思维,科学尚未有答案,但有推测称这可能涉及视觉皮层内部和周围区域的功能分离。
非心盲者很难想象我们这些缺乏“心灵之眼”的人是如何记忆事件的,因为我们无法回忆起心灵图像、气味或声音。科学家们也开始尝试解开这个大脑之谜。一篇由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丹妮拉·帕隆博(Daniela Palombo)课题组在2015年发表的论文标示出一种新的综合征,他们称之为“自传式记忆重度缺失”(Severely Deficient Autobiographical Memory),简称为SDAM。[3]SDAM者无法在脑海中重温过去。虽然这种状况在普通人群中很罕见,但有初步调查暗示了它与心盲的关联。2000名SDAM者中,高达51%的人同时是心盲。
我有类似的亲身经历。我的过往生活——就算我能够回忆起——感觉遥远且无感觉体验可言。大多数在职心理医生尚未了解SDAM这一新发现,因此像我这样的人目前只能自我诊断。但研究人员描述的症状与我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体验相符。我把回忆总结成关键事实,而非第一人称的“心灵电影”。当被突然问及我肯定有过的经历时——比如一个童年生日聚会——我的脑海当即一片空白,就好像我的情境记忆被归档到一个没有索引的文件柜中。许多记忆都还在,但若是没有非常具体的提示,检索它们简直难如登天。通过一些推测(当时我住哪?和谁在一起?),我回想起的细节可以勉强勾勒出一些地点和非视觉化事实:我大约在11或12岁时在我们乡村花园里举办了一个大聚会;有蛋糕;有很多孩子跑来跑去……仅此而已。
这一切如何影响着我的生活呢?答案可能令人惊讶,它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至少没有妨碍我的生活。人们很少过问我几十年前聚会的事,这让我如释重负。即便要形象地描述场景或人物,我也有足够的“语词素材”和相当的口才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不需要在脑海中复刻真实的画面。
研究人员的普遍共识是,心盲不符合残疾的标准,而且心盲者大体上有着与其他人一样的生活工作能力和成就,巴黎索邦大学两名研究人员最新的一篇论文似乎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点。[4]他们让参与者(包括许多心盲者)完成一系列在脑海中比较形状、颜色、文字、面孔和空间关系的任务。在所有测试中,心盲者有着和其他参与者一样的准确度,尽管他们花费的时间稍长一些。这也许是因为心盲者采用了不同的、更间接的策略。
即便如此,一些人发现自己是心盲仍会感到绝望。我见过一些人说“我这辈子就是一个谎言”,或者“正是这个东西毁了我的婚姻”。我虽然没那么悲观,但还是能感同身受。心盲和SDAM可能确实没有导致日常生活的不便,但它们的微妙影响难道不会日积月累吗?它们难道不会引起其他令人羞愧的弱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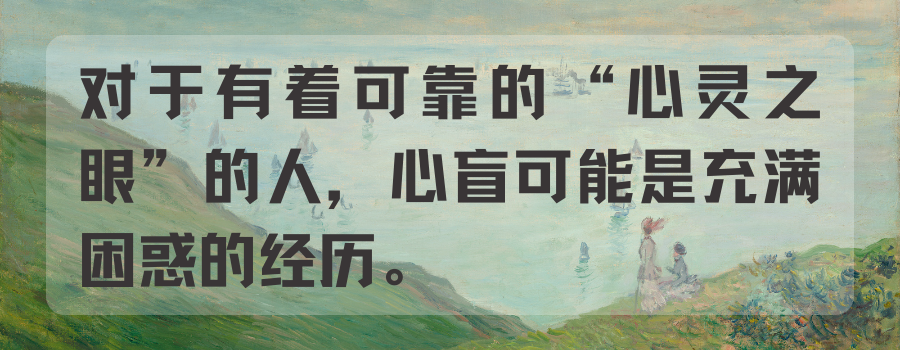
对于许多我们这样的人,发觉自己心盲可能会导致某种自我意识危机。突然间,你开始质疑日常作为的方方面面,几乎情不自禁把你的种种问题归咎于先天心盲。是不是因为心盲,我才不得不靠参考实物才能画图?我不擅人际互动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SDAM?如果不心盲,我是否就不那么容易“社死”?这些关联假设大多未被实测,更不用说得到研究发现的背书。然而,几乎所有我接触过的心盲者都会这样想。但似乎每个人都将自我质疑集中在自我否认的方面,将不足归咎于此。
我已经学着接受心盲的多样性,并且希望能够将它广而告之。研究者高桥淳一(Junichi Takahashi)也一样,他是第一个了解我情况的研究者。高桥是福岛大学的心理学家,也是日本第一批关注心盲的科学家之一,而我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日本生活。他在一个网站上提供了VVIQ调查,正是这一调查使我确信自己是心盲。我联系了他,开始了解更多有关视觉想象及其缺失的科学知识。
高桥并非将心盲视为一个单一现象,而是试图澄清它的多样性。在2023年7月,他和几位合著者发表了一篇关于心盲亚型的论文。[5]大部分之前的研究仅依赖VVIQ问卷来确认心盲的个体,而高桥和他的团队则向同一批受试者提供了一系列额外的心理问卷,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其中一个问卷调查了多感官心智想象的生动性,包括听觉、嗅觉等。心盲者能否在脑海中重现父母的声音或者奶酪蛋糕的独特味道?另一个问卷测试了被试的思维风格是倾向于靠语言(更多地依赖语言来理解事物)还是靠视觉(更多地依赖图像)。还有另一个问卷用于检测“面盲”,即无法识别人脸。
他们的统计分析显示出所有这些因素某种程度上是相关的,但又不是完全相关。例如,他们的许多心盲受试者缺乏所有的“心智感觉”(mind senses),但有些人确实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声音、味道或其他非视觉体验。该论文还发现,心盲者中更常见地出现“脸盲”(40%),而对照组只有20%,但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心盲特质。
然而,讨论这些问卷和自我评估都引发了一个老问题:我们怎么确认心盲客观存在,而非特定形式的心理否认(psychological denial),或是对相同内在体验的不同解释呢?
心盲首次被正式提出时,一些研究人员质疑,在很多情况下,所谓的想象力缺乏是否并非先天特质,而是一种心理病理问题,比如神经症或面对创伤的防御机制。一种“哲学语言障碍”更是将问题复杂化:语言是我们比较内在体验的唯一媒介,但我们可能用不同的话谈论着相同的事情。我们无法确认这一点,至少曾经如此。甚至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早在心盲一词出现60多年前就思考过这种情景:如果一个人声称他们无法想象一个图像,但仍然能够画出来,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的头脑中真的发生了不同的事情吗?
现在,科学家们正在寻求具体客观的数据来回答这些问题。“甚至在心盲成为研究对象之前,研究人员就试图区分开VVIQ得分较低和较高的人,并发现两组人在某些任务上的不同表现,” 高桥向我解释道。“此外,很多研究显。